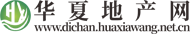陈翠梅导演的《野蛮人入侵》终于在中国内地上映了。
负责任地说,这是一部至少需要二刷的精致小品,基本已经锁定了笔者的年度十佳。
《野蛮人入侵》曾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并斩获大奖,它与上海渊源颇深。2019年6月,天画画天影业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合作项目“B2B电影计划”。
 (资料图)
(资料图)
这个计划邀请亚洲六位导演——蔡明亮、张律、翁子光、陈翠梅、石井裕也、杨瑾以“爱情征服一切”为主题进行长片创作。
在石井裕也完成《只能唱的心声》(2020)之后,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野蛮人入侵》也终于亮相。
《只能唱的心声》(2020)石井裕也
B2B英文全拼是Back to Basics,大意可理解为“回归本初”。计划的主旨鲜明而大胆:六位导演将以低成本挑战电影艺术的界限。
低成本,还要挑战电影艺术的界限。他们做得到吗?
陈翠梅做到了。她用这部创意爆棚,回味无穷的《野蛮人入侵》告诉所有人:一百万人民币,既能够守住一个电影项目的底线,还足够挑战艺术创想的极限。
《野蛮人入侵》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但却是一部叙事层次非常丰富的影片。电影的主要故事可以描述为单身妈妈李圆满(陈翠梅)带着儿子宇宙来到海岛。
她是一位年届中年的女演员,受老搭档胡子杰(张子夫)导演之邀一起合作一部新电影。
影片前半部主要呈现子杰和阿满筹备影片的过程,重点跟拍了阿满接受武术训练的艰辛和她想要兼顾工作和照顾儿子的两难境地。
当故事行进到一半,电影的筹备和阿满的命运都遭遇重大挫折。影片随之展开一段“戏中戏”,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他们所拍摄的电影当中去。最后,随着新片拍摄接近尾声,我们和阿满一起,离开电影回到现实生活。
阿满的现实生活与新片中的故事这两个世界,既不是以段落式进行切割再乱序拼贴,也不是刻意模糊界限去故弄玄虚。
这样虚实结合的烧脑设定,在《野蛮人入侵》中被陈翠梅处理得行云流水,举重若轻。
她让现实和电影排成两道渐进的线,二者越走越近,在影片中段开始交织,而后再次分开,渐行渐远。整体看下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穿越”体验。
“穿越”不仅出现在素材的结构编排上,更通过无数对应的细节被编织进入《野蛮人入侵》的影像肌理中。
饰演导演的张子夫在幕后特辑中说,《野蛮人入侵》是一部充满了映射的作品。没错,导演和演员现实中的生活、他们口中所讨论的那尚未诞生的影片都和观众在中后段得以亲眼看到的“完成片”之间形成了多重映射。
现实中的阿满是个柔弱的母亲。年龄削弱了她的身体活力,感情的失败压抑着她的精神意志。
从前往后看,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在极端环境里逐渐突破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极限;而从后往前看,也就是从后半段“戏中戏”里面那个身手敏捷,身份成谜的女特工往前看,前半部影片就是一个神秘女英雄的成长历史。
在中学时就读过三遍《红楼梦》的陈翠梅看来,电影和做梦自有相通之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观影过程中,那种无法将陈翠梅、阿满,女特工分清的梦幻萦绕,隐约正是无限接近电影之魔法的状态。
陈翠梅其实不仅阿满这一个分身。导演子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她的一个精神投射,所谓导演和演员的一体两面。
电影开篇,陈翠梅便借一场导演向演员阐述拍片初衷的戏,向观众道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核所在。
这个段落写得实在太精彩,相信也会是吸引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的戏眼:
子杰:宫本武藏到了很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来挑战他。他们约好第二天中午在山上决斗。但是宫本武藏一直到太阳到了西边才出现。年轻人非常生气,宫本武藏背对着阳光,在决斗的关键时刻,故意让年轻人对着刺眼的阳光,一瞬间把他杀了。”
阿满:这不是胜之不武吗?”
子杰: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剑就是一切。对年老的宫本武藏来说,一切都是剑。阳光是剑,时间也是剑。
阿满:所以?
子杰:以前年轻的时候,电影是一切。现在年纪大了,一切都是电影。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活根本就是一场电影。
《宫本武藏:岸流岛的决斗》(1956)稻垣浩
《野蛮人入侵》可以视作一次对电影媒介的审视,同时也是一个电影人为了创作忘我投入,经受身心双重洗礼的过程。
如果电影是一切,一切是电影,那么“我”也是电影吧。现实与电影之间的多重投射之下,更多的其实是照见我们自身。
我们一路随着子杰和阿满经历并不顺利的前期筹备过程:拍戏戏红人不红、预算捉襟见肘、选角遭遇私人生活冲突、金主想要让自己热捧的女演员带资进组等等,都是电影人对这个行业的自我解嘲。
子杰立志不拍“洪常秀电影”而要拍“东南亚的《谍影重重》”。这在一开始听来是玩笑话,然而当电影慢慢展开,观众会发现,这非但不是一句荒唐言,反而又是一句干货满满的中心思想——他们要做的就是对《谍影重重》的一次相当深刻的解构。
他们不仅要学《谍影重重》硬桥硬马、拳拳到肉的动作戏,还学到了它最核心的设定——那便是“我是谁”的问题。
《谍影重重》系列创造性的写实打斗风格,让动作片焕然一新
阿满经历魔鬼训练,摸爬滚打,最终在海滩上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出师。一段将近一分钟的长镜头肉搏戏,看得人攥紧拳头,这对演员体能上的要求是可想而知的。而导演/演员陈翠梅坦言她就是为了流这些汗水而写这些场面的。
阿满问师傅,什么是“自己”。师傅徐徐走过来,对阿满猛地出拳,击到她头破血流。
师傅随即问:是哪个挨打?是哪个感到痛?又是哪个知道要挡?
马来西亚独立电影人、重要电影推手李添兴(James Lee)饰演了师傅一角(右)
当肉体被逼近极限,体肤上的失能和失控才终于能将一个人的灵魂真正剥离出来。
终于,当阿满发现了“她自己”。《野蛮人入侵》也从照见电影,照见自身,来到照见存在上面来。
影片中穿针引线的那些迷影梗,其实也全都指向身份和“我是谁”的问题。除了醒来就带着遗失的身份的杰森·伯恩,“戏中戏”里面带起了红色假发的阿满和她的失意,也扣上了《穆赫兰道》——恰好是一个做梦的故事,一部对女性身份和电影媒介进行阐释的影片。
《穆赫兰道》(2001)大卫·林奇
影片让我们带入了阿满的生活,看到她作为演员、妈妈,女性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多重蜕变。可阿满究竟是谁呢?是演员?是母亲?是前妻?是女人?还是什么?
《野蛮人入侵》的果敢之处就在于陈翠梅大量投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真实体验。她自己在怀孕生子后,开始意识到男女生理上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公平,感觉自己的身体像《异形》一样,被一个异性侵占,吸食养分,破体而出,最后成了一片废墟。
通过学武,她要重拾自己的身体,重新宣告自己身体的主权。
所以《野蛮人入侵》其实缘起于孩子——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对文明世界的一次入侵。
儿子宇宙的诞生,破坏了母亲身体的秩序,进而颠覆了她的精神世界。整部影片看下来,是一个人重新塑造自我的故事。
陈翠梅说她写剧本,都是先想好结局。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是子杰走在水上,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他挥舞着阿满留下的两只训练用的“剑”,最后把“剑”抛掉了。
拍这场戏时,陈翠梅不断跟要求西班牙摄影师鬼佬给她空白,一片空白(Keep it empty.I want emptiness.)。
做音乐时,她跟马来编曲Kamal说再减一点,再空一点(Less, minimize the music.)。
调色时,对泰国调色师Ice说再白一点 (Can it be whiter? emptier?) 。
跟混音师Rit说:再安静一点……
这自然让人想起开头“一切都是剑”的宫本武藏。
通常拍电影,创作者都在不断使用各种技术武器来武装自己。在经历“野蛮人入侵”之后,脱胎换骨的陈翠梅则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一切都是剑,没剑也可以杀人。如果一切都是电影,那么有工具没工具都不重要。
因为最后画面上剩下的那一个人,就是电影。
下一篇:最后一页
X 关闭